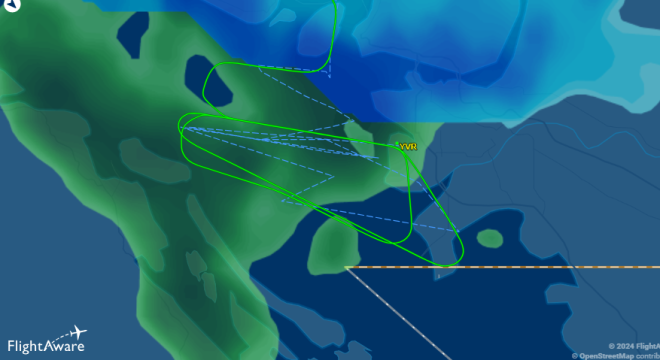实际上,那天我是作为一场文学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人,正赶去参会,为此会议举办方还向我支付了酬金。但正因为会议主办方支付了我此次行程的所有开销,美国海关对我说:“我们有更多问题要问你”。于是我就被带到了一间小屋子,和另外20几个人一起等了1小时40分钟之后,我又被盘问了15分钟。

本文作者、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曼姆·福克斯(资料图)
那个房间和普通的等候室相似,只是更为阴森恐怖。墙上贴着一张不太明显的告示,警告大家不能使用手机。在这个房间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人都被大声训斥:“别用手机!”房间里的警察态度粗鲁,他们似乎除了训斥不会讲别的话,而且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监视,毫无保留。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真让我做为人类感到羞耻,实在太可怕了。
那天有一位大约80岁的伊朗老妪,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小开衫,坐在轮椅上,而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却对她大吼:“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反复厉声吼叫之后,她终于大致猜到了对方的意思,这才回答:“波斯语。”我当时就在想,老天,帮帮她吧,作为伊朗人,她面临怎样的命运?
还有一位台湾女性,海关大吼着盘问她的收入来源,但她没听懂对方的问题,于是那个海关官员就冲她大喊:“你的钱从哪儿来的?从树上长出来的吗?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的场景太可怕了。
还有一个妇女带着婴儿,然而这个房间既没有盥洗室,也没有饮用水。设想,要在这个房间待上几小时,胸前捧着一个哭闹的婴儿,或者急需给孩子喂奶,如果是我,我的天……我绝对承受不了,这个房间散发出的非人道气息,让我心如刀割。
当他们终于叫我去询问时,我正在重读一本40年前自己就读过的小说——谢天谢地我手边有本小说。书名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19世纪的小说适合长途飞行时阅读,能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但后果是,我看得太投入,竟然没听到他们叫我的名字。我前面一个女子回过头说:“他们在叫福克斯”。然而我并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小隔间接受询问,正在犹豫之时,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了,挡在我面前并冲我大吼:“不是这儿!去那里!”我客气地道了歉,说我因为看书看得太入迷所以没听见自己的名字,他回答道:“那你想让我干吗?让我在这儿等着你看完小说吗?”——他的声音洪亮,傲慢无礼,我真得被他吓住了。
他们的问询方式也非常可怕。如果他们看到我手提箱里的书,就会知道一切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我带了一本自己的新书《我也是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主题是移民,欢迎人们到另一个欢乐的国度生活。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大人生信条:我向来看重包容性、人性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我的包里还有自己的另一本书《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于是我就跟美国海关讲了我带了些什么书,这些书所表达的包容主义内涵,而对方却冲我大吼:“你以为我不识字吗!”
对方年纪估计连我的一半都不到——我虽然还没到70岁,但也早就不年轻了——然而,我全程都是站着回答问题的。质询过程充满火药味,令我胆战心惊,为了安抚我怦怦乱跳的心,我不得不将右手的手掌捂住胸口。
那些海关人员也没有丝毫歉意。当对方终于得知我的《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是澳大利亚政府赠予乔治王子(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长子——观察者网注)的官方礼物之一时,他伸出手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福克斯女士”。问了那么多问题,他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接近崩溃,差点晕倒——这种转折实在太诡异了。
我全程客客气气、彬彬有礼,饱受他的诘难,他却竟然说“很高兴”,让我大跌眼镜——他这般百般刁难,竟然还享受其中,简直变态。
那一刻,我真得很讨厌美国,我讨厌那个国家。其实,那已经是我第117次赴美了,我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都非常慷慨热心,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待我很友善。我也知道,这份恨意过一两天就会淡去,但交朋友绝不是这样子的。要知道,澳大利亚可至始至终支持着美国人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今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澳大利亚人,实在是太过于忘恩负义。
那天,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气得发抖。我打电话给一位美国朋友,她是个编辑,我在电话里向她哀嚎,她让我不妨将这段经历写下来——于是我写了两个小时。那晚,我本来打算睡足8个小时,却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就被自己哭醒了——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我回到澳大利亚后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道歉信,信的内容让我安心许多。同时,我也接到了许多美国人和美国作家的来信,对我表示安慰与支持。
我能够理解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也许并没受到良好的训练,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拥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不管态度多恶劣、多具有攻击性都不用担心后果。于是他们像发了疯一样。一个公职人员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却没接受相应的训练,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能说一口流利、清晰的英语,他们都能让我感到无助、渺小,那么其他不会说英语的人境遇又会如何呢?我不断地思考,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为母语的女性,又是白人,我都会遭受这般待遇,那么其他人种呢,他们又会受到怎样可怕的对待?
这一点让我伤心欲绝。要知道,我被从队伍里拉出来询问,并非因为我是个革命积极分子——然而,我的天,我觉得我现在已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革命积极分子。我在自由、尊严的前线战斗。如果我们不起身大喊,理性将无法取得胜利。因此,我将放声大喊,为人权怒吼。
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以前仅仅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分子,但这次事件后,我变成了革命主义者。我不能让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自此,我不会坐在沙发上自艾自怜,相反,我会给政治家写信、给各路人士致电、给报纸投稿、参加电台节目——我不会再保持沉默,不会再保持被动,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