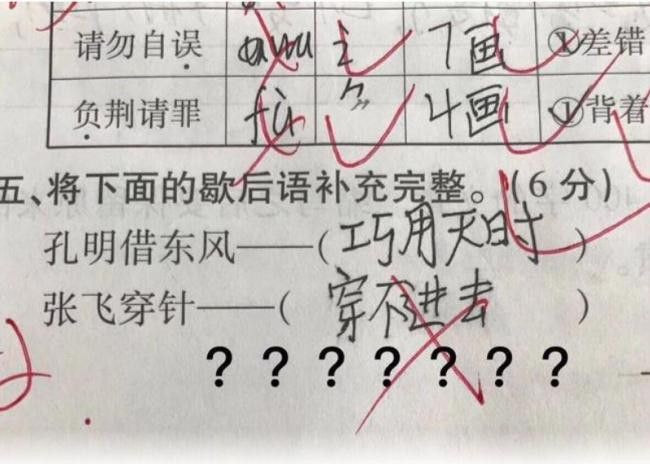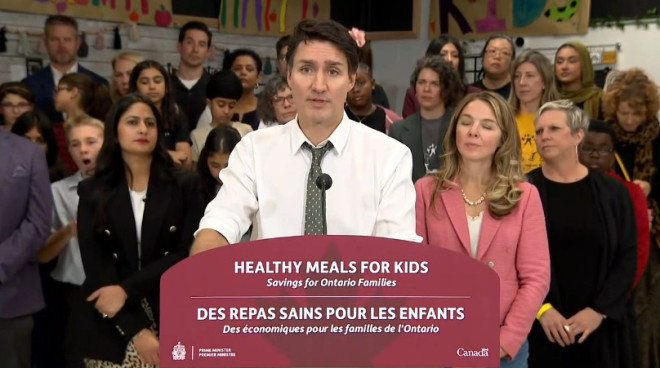第一次对男客(注:即嫖客)做访谈,听到这个问题,潘绥铭的学生杜娟傻眼了。当时二十出头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夺门而出,但最后她还是坚持问完了问题。
这个情节,出现在新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它是一群性社会学学者多年来研究“红灯区”的经验总结,写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姐”)的关系问题。作者是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以及他带过的研究生(后者通常自称“潘门弟子”)。
他们要解决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怎么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怎样控制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放低身段,自甘堕落”
怎么接近研究对象?最开始,研究者请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疾控部门牵线,用“访谈费”和礼品换取小姐们开口。但此举效果极差。
事实上,小姐们对这些闯入者非常反感:这等于一上来,就给她们插上了一个“潜在艾滋病传染者”的标签。
研究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小姐们。比如“大师姐”黄盈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得到朋友帮助,在“红灯区”租了个住处,楼下就住了几个小姐。利用一次晒衣服的机会,她成功搭讪上其中一个,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爆口“吹箫”——据其说这是潘门弟子平日“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
2005 年以考研总分第一名得入潘门的王昕,搞定一个“看场子”的男经理,成功采访到了小姐。她的师妹杜娟因为一位“妈咪”的帮助,也获得了接近小姐们的机会。
她们共同的经验是“放低身段”,用王昕的话说是“示弱”,黄盈盈则说得更为直白:要“自甘堕落”。在与小姐相处时,王昕会刻意不提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而是自称“学生”。而小姐们则能从这个称谓上获得优越感:你们学生是靠家里人养活,我们好歹也是自食其力。这样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但在艰苦突破了第一关后,潘门弟子很快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给学生讲课时,潘绥铭每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查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被敲诈、被骗、被引诱下水……只有一个学医的男生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
为什么?很简单。以调查者的年龄、身份,能平等地对待小姐——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你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因为在她的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被人爱上是好事,为什么又被认为“最危险”?这就涉及到研究者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伦理困境。用潘绥铭的话说,就是“因为没办法回报 ,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
这种因无法回报而生出的愧疚感,曾经困扰着王昕,以致于让她一度需要心理疏解。
“(社会调查伦理)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我们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她们……”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一次刻骨铭心的误解

某会所包间。摄影/射小箭
在书中,王昕着重写了那个帮了她大忙的男经理。说是经理,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羞涩的大男孩。他二十出头,只有小学文化,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男孩在KTV负责“看场子”,因此和小姐们的关系很好。
王昕还记得,男孩把她引见给一个小姐之后,开始也坐在那儿听,后来王昕和小姐谈到性交易的一些具体行为,他就脸红了,主动离开房间。
王昕与男孩接触时,还曾闹过一个乌龙:有一天,男孩带王昕在KTV里转悠,王昕突然肚子痛, 刚要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男孩把她拦住了,用钥匙打开了一个豪华包间,对她说:“姐,你用这间吧,这里干净。”
但王昕却将信将疑,她拿不准这是男孩向她“示好”,还是别有图谋。就在她完事后准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开不了,“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
快哭了的时候,王昕一下把门扭开了。原来,是她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前一秒是快被自己吓哭了,后一秒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出来之后,王昕发现那个男孩蹲在楼道里,背对着她,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
这次误会让王昕刻骨铭心。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重要,但真正建立信任又是如此之难。而这种隔阂和误解,并非仅仅处在她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实际上,在同事、朋友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男孩的帮助下,王昕的调查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她要离开那个城市时,请男孩去饭馆吃饭以表谢意。席间,王昕频频举杯,可男孩却每每抢过去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说:“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离开饭店时,王昕才注意到男孩一直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当地很贵的水果——红毛丹。“路上吃,买给你的。”男孩说。“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王昕写道。她知道,男孩天天上夜班,一个月还挣不到两千块钱。
王昕说,后来男孩曾经给她发过短信,但最终失去了联系。“不伤害”是伦理底线

一小姐在休息室梳妆。摄影/射小箭
十年前的那次调研中,王昕曾采访一个读书的小姐。那是在一个专门供小姐休息的包房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看电视,只有她手里拿着一本《读者》。
这个访谈非常成功,对方边说边哭,王昕边听边哭。但是第二次,当王昕再遇到那个小姐时,却发现对方对她非常冷淡,一直躲着。
王昕困惑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找到了原因。
她认为,那次访谈的“成功” ,并不是由于她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她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对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她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对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她卸下心防。
王昕进一步悟到,她的再次出现,会让对方联想到那个满是伤痕的、脆弱的自己,而她还要在那个环境里生存,她必须正视现实,所以只能再次披上盔甲。
在《我在现场》中,王昕作了如下反思:
“(在调查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伤害” 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事实上,十年过去了,王昕与当年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断了联系。她认为这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应该的。当年的研究对象很多都不再从事性服务业,她们不愿将过往的经历示人,因此如果主动联系,对她们会是一种打扰,甚至会是一种伤害。
而不伤害,是社会学调查的伦理底线。从恐惧、后怕到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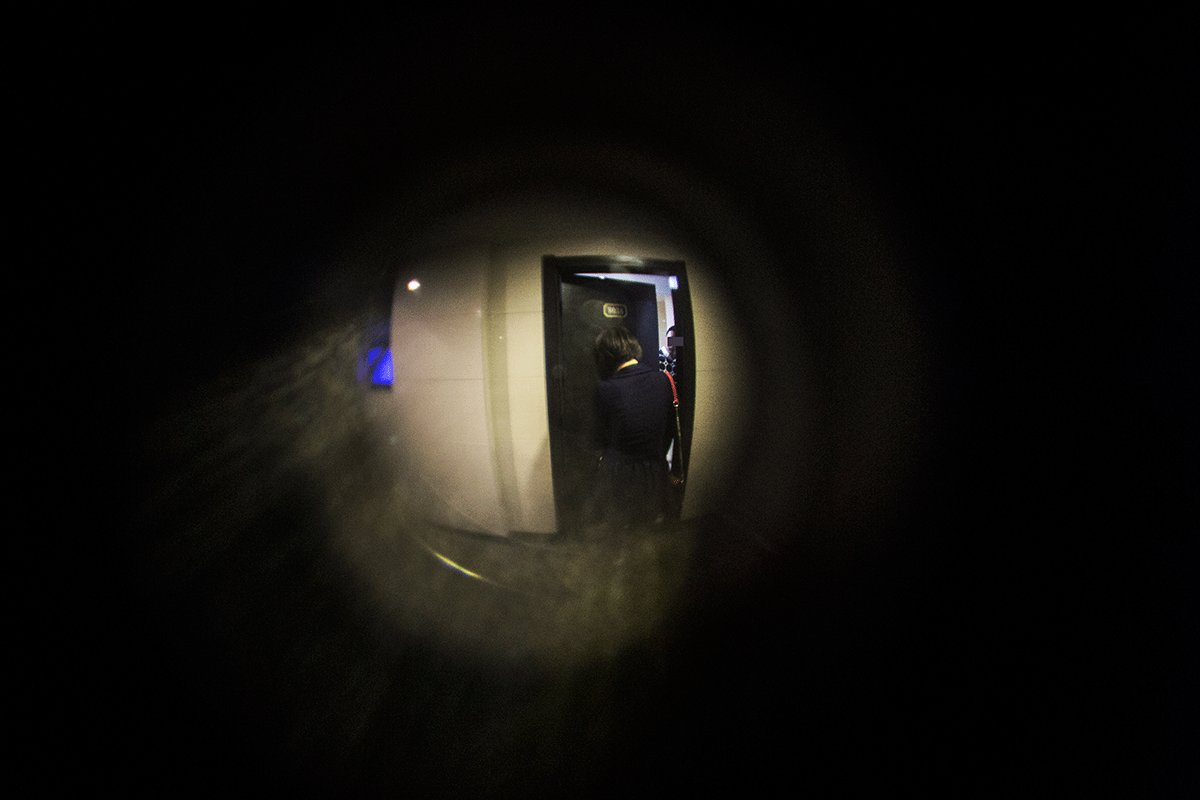
某酒店内,一小姐上门提供服务。摄影/射小箭
对于潘门弟子而言,在从事“红灯区”的研究时,除了需要大量采访“小姐”,还需要采访嫖客(研究者们通常称之为“男客”),以便使研究更为立体、丰满。
如今快是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的杜娟,对最初和男客做的访谈印象深刻。当时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面对一个陌生男人谈性,她害羞、害怕、紧张、兴奋。但对方却十分坦诚,几乎有问必答。
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对方突然抛出这么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杜娟在书中写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
但杜娟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不成”,之后竟然又问了几个问题,而那个男客——一个卖沙子的小老板——则在尴尬中回答完了她的问题。
多年以后,再度回想这个场景,杜娟主要不再是恐惧和后怕,更多的是自省。如今,她已经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提出跟她上床的“男客”:“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自然会有这样的念头。”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
杜娟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部分小姐排斥那些给客人做“口活”的小姐,“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她引用一位小姐的话说。“她们(中有一些)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
在潘门弟子中,仍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的人不多,杜娟是其中之一。对于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把握分寸的观点,她本人并不敏感。她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如果机缘到了,研究者与小姐发生爱情并不奇怪。
“老师与学生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杜娟说,“师生恋最后发展到结婚有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