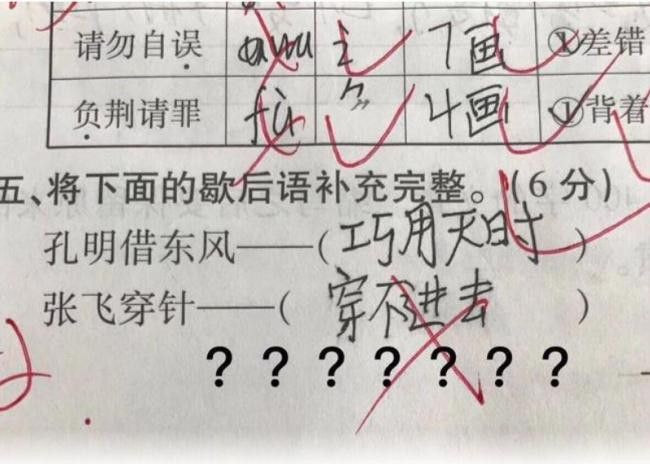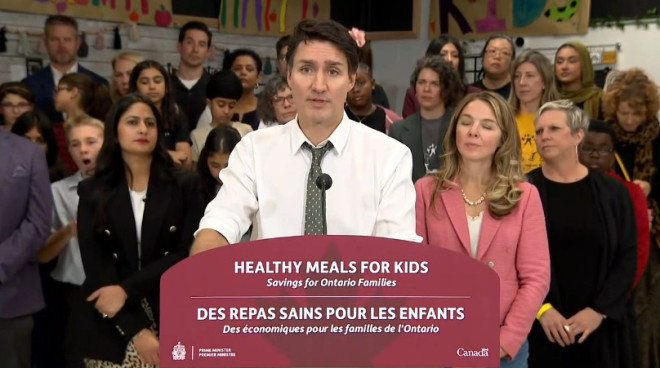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余秀华在横店这处农舍里长大,并开始写诗。
中国横店——在中国,她已经成为读者最多的诗人之一——甚至被称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她41年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栋砖房农舍里,门前有树,周围是麦田。
大多数日子,她会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一条土路,到一个池塘去喂鱼。她用一把不太顺手的镰刀割草,喂她的兔子。在房子旁的阴影里,她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写作,努力控制她颤抖的身体——自从降生在中部省份湖北的这个村庄,她就一直忍受着脑瘫的折磨。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谈到离婚后的生活时,余秀华说:“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感觉很好。”
然后,在2014年,她的生活改变了。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那一年,余秀华在她的博客上发布了这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了轰动。她的诗歌被中国著名的文学杂志《诗刊》的编辑刘年发现。刘年写了关于她的文章,并转载了她的作品,到2015年2月,她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后者成为了30年来最畅销的中国诗集。
一大批记者蜂拥到她的农舍,想要亲眼见见这位把情欲热望写得如此生动的残疾农妇。她被任命为附近钟祥市的文联副主席。刘年邀请她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一个读诗会,在那里,她接受了《人民日报》、央视等国家新闻媒体的采访。
去年,电影导演范俭拍了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她的另一部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也出版了。今年,她第一次离开中国,出现在斯坦福和其他美国大学的电影放映会和研讨会上。
“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出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亚特兰大莫斯洛特学院(Morehouse College)的教授、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沈睿在《月光落在左手上》的序言中写道。
余秀华说她并不喜欢别人将自己和狄金森做比较,她从未读过狄金森的作品。近日的一天下午,她在横店的家中说,她对世界文学的了解有限。
余秀华在近30岁的时候开始写诗,她说,在那之前,“我很少读文学。2006年以后,我才开始在手机上看到更多的名著,但是在读它们之前,我就知道如何写作了。”
“我喜欢写诗,因为它们简单,没有多少字,”她嘴巴抽搐着,断断续续地说道。“这适合我,因为我很懒。”
她现在和父亲住在一栋新建的两层楼房子,距离他们的旧农舍几步之遥。最近一次村里进行翻修的时候,大部分的老房子都被推平了,居民们搬到了新居,但出于对当地名人的尊重,她家老宅被保留下来。
她作为一个作家,通常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女性、农民、残疾人,但她对自己的名声和这些标签并不在意。她还说自己对读者的反应没感觉。
“最重要的是,写诗意味着面对我自己,并不是面对别人。”她说:“这是在表达我自己。无论他们回应我的诗与否,那是其他人的事。跟我无关。”
读者的确做出了回应。在《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她写道:
“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这首诗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人谴责它淫秽,其他一些人却称赞它表达了一个主动“睡”别人的女性的女权主义声音。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诗刊》编辑刘年写道。“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余秀华1976年出生于横店,没上完高中。19岁那年,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和一个年长她12岁的建筑工人结婚。父母担心她永远都无法照顾自己。27岁那年,她开始写诗。
“我需要做点事情来提神,”她说。“每天,我写一两首诗,就会有成就感。”
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关于她的农村生活的。在一首有关她父亲种的小麦的诗中,她写道:“你的幸福是一层褐色的麦子皮,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
她也经常以爱情和它带来的混乱为主题写诗。在《唯独我,不是》中,她写道:
“我相信他和别人的都是爱情。唯独我,不是。”
前述电影导演范俭说:“你能在她的诗里读出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她渴望爱情,但又感到害怕。她其实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
余秀华承认自己的婚姻不成功。“我当时太年轻了,不懂,”她说。“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我们的性格一点都不和。”
多年里,她一直想离婚,但她丈夫不愿意。她说,一个原因是经常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的丈夫回来后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去年,在收到大约九万美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后,余秀华给他买了一处房屋,两人离婚。他们的儿子在湖北省会武汉的一所大学上学。
“我母亲一开始不高兴,但后来就好了,因为她看到我真的很快乐,”余秀华说。不久后,她母亲因癌症去世。
谈到离婚后的生活时,余秀华说:“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感觉很好。”但她对自己依然持否定态度。
“我真的长得难看,”她说。“所以找不到男朋友。”
暂时,她还有诗。
“诗歌是什么呢,”她在《月光》的后记中写道。“我不知道,也说不上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
Tang Yucheng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